范西纳的非洲史研究
刘伟才
内容提要 范西纳是现代非洲史研究第一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以口述资料、非洲器物以及语言资料为基础,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等对非洲史进行研究,提出相关理论并进行实践,在刚果河流域、大湖及赤道等地区历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使一些一度被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史家认为“无历史”的地区变成“有历史”,也开辟了对这些地区的历史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道路。与此同时,由于口述资料本身的缺陷以及语言、考古等资料的不充分,范西纳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有待突破。
关键词 范西纳 非洲史研究 口述资料 语言资料 器物资料

让·范西纳(Jan Vansina)是现代非洲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积极探索非洲史研究的理论并勤于实践,在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以非洲器物和语言资料为主、多资料多学科相结合研究非洲史方面进行了重要尝试,使“无历史”的非洲变为“有历史”,同时为非洲“有更多的历史”开辟了一条道路。
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并提出相关理论和方法是范西纳最引人注目的贡献。部分国外学者对范西纳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方法论和实践给予充分的肯定,特别承认其在非洲史研究开拓阶段的突破性意义。与范西纳同时代的著名非洲研究学者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曾撰文谈及非洲史研究开拓阶段的艰辛,称当时有一系列的资料和技术手段需要开发利用,而范西纳适时出现,以两篇关于库巴口述历史的文章为突破,为非洲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可范西纳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理论和方法。曾与范西纳同在比利时中部非洲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Central Africa)工作的卢克·德·休奇(Luc de Heusch),并不认为范西纳能被当作真正的历史学家。他说:“我认为民族学—史学学者,特别是让·范西纳,过于自信,认为他们能够把卢巴王国(Luba)的传奇性记录当作历史资料来进行解释。”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持反对观点者是范西纳的学生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他在范西纳指导下搜集口述资料,对安哥拉的一个古王国进行研究,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口述资料不应该被用文字来解释,研究者只能通过对社会组织和社会观念进行研究后对口述资料的叙事环境进行解读。
国内学者对范西纳及其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些介绍性的文字。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学者对范西纳的《作为历史的口述资料》一书进行了译介。此后,国内学者开始较多地提及范西纳。例如,李安山在《国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古代史的研究(1960—1990)》中,对范西纳的口述资料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介绍;李保平在《试论非洲口头传说中的史实与非史实》中,对口述资料的特点及其运用的优势和局限进行了介绍和简单分析;舒运国在《非洲史研究入门》一书中,辟专节对非洲口头文化与口述资料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列举简述了非洲的几种主要口述资料,并对范西纳的研究和部分著作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北京大学亚非所曾在研究生教学中加入与范西纳相关的内容,并译介了范西纳的文章《非洲王国之比较》。
范西纳创建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理论并进行了相关实践,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止于此。在搜集并利用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基础上,范西纳还尝试从非洲器物、非洲语言等入手,对非洲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以非洲语言为资料进行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学界对范西纳的介绍和认识往往止于口述资料一端,强调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但却忽视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忽视了范西纳本人对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和扬弃,二是忽视了范西纳以口述资料之外的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尝试和成果。本文将力求全面地论述范西纳关于非洲史的研究,试图呈现出更完整的范西纳。

范西纳与现代非洲史研究的兴起
除北非、靠近北非的西非部分地区、东北非和东非沿海地区外,非洲大片地区长期以来被外界视作“无历史”的黑暗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对非洲史进行研究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者和殖民宗主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英国首先开始考虑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非洲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并选定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研究人员主持相关工作,该院的西里尔·菲利普斯(Cyril Philips)被派往东非调研。菲利普斯对非洲史资料搜集和保存工作的薄弱感到惊讶,同时他也看到,英国人研究的非洲只是英帝国的非洲,而不是非洲人的非洲。调研结束后,菲利普斯提议就非洲史研究设立两个专门职位,一个职位的担任者留驻伦敦大学,另一个则去往非洲。1948年,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er)被聘为东方与非洲学院的非洲史讲师。另外一个被选聘的是约翰·费奇(John Fage),他于1949年前往黄金海岸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Gold Coast)。1949年,奥利弗也去往非洲,先到加纳,然后前往乌干达和肯尼亚。1950年返回伦敦后,奥利弗设立了非洲史学术讨论会,开始培养首批研究生。正是奥利弗和费奇这两人,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非洲史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1948年,尼日利亚的肯尼斯·戴克(Kenneth ODike)开始在尼日尔河三角洲收集口述资料用于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同一时期,肯尼亚的巴斯维尔·奥戈特(Bathwell AOgot)也在着手搜集并运用口述资料撰写罗人(Luo)的历史。“一西一东”开展的这两项工作,可以说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但是,此时非洲学者的工作并不受重视,以口述资料为基础写史也得不到欧美学者的认可。范西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非洲史研究领域。
范西纳于1929年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他先就学于一个宗教机构,后进入鲁汶的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在鲁汶大学,范西纳初修药学,后转向历史。大学毕业时,范西纳应聘成为王家比属刚果博物馆(The Royal Museum of the Belgian Congo)的一名人类学调查员,随后去往刚果,成为比利时中部非洲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Central Africa)的一名人类学调研工作者。在赴非之前,范西纳先被派往英国接受培训,主要是学习人类学和人类学调研工作的基本知识,并初步学习了非洲的土著语言。1953年,范西纳开始在比属刚果的库巴地区(Kuba)开展工作。他参与并记录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各种仪式,学习并研究当地语言,搜集口述资料。在这期间,他还通过参加集体项目、研讨会、学术会议等,接触了当时非常活跃的来自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史、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非洲研究学者。
1956年,范西纳回到比利时,以自己在刚果搜集到的资料为基础撰写论文,并决定以此申请历史学博士学位。范西纳最终完成的论文题为《口述资料的历史价值:库巴史的应用》(The Historical Value of Oral Tradition:Application to Kuba History),这一论文以口述资料为基础来写库巴地区在殖民时代之前的历史。然而,在申请博士学位的问题上,范西纳遇到了麻烦。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仍然认为殖民时代前的非洲没有历史,口述资料的价值和有效性并不被认可,而且当时在比利时也没有正式的非洲史学科和被认可的非洲史学者。当范西纳申请按历史学论文的标准和程式来答辩并获得相应博士学位时,鲁汶大学校方不同意,理由是这一论文属于民族志而不是历史学。在范西纳的一再要求下,校方又声称没有相应的学者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来主持这一论文的答辩。但范西纳仍然坚持,最终他的要求被勉强接受,论文被认定属于历史论文,答辩也在1957年10月举行并获通过。但是,质疑仍然存在,范西纳仍然被看作一个民族志作者,而非一个历史学家。
尽管如此,范西纳的工作仍然引起了注意,奥利弗和费奇邀请范西纳前往伦敦大学。与此同时,另一位意识到非洲史研究机会的美国人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也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最终,范西纳选择了菲利普·柯廷。1959年,范西纳赴威斯康辛大学。此后,范西纳一直在威斯康辛大学任职,他除了调研、搜集、整理各种资料并进行写作外,还与柯廷一道创建并推动了以非洲历史为主的“比较热带历史项目”(Comparative Tropical History Program)和具有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双重功能的“非洲历史项目”(African History Program)。与此同时,他还从国际层面参与非洲史研究事业,逐渐成为知名的非洲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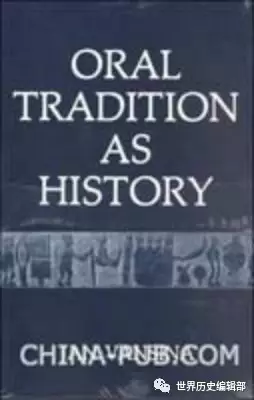
以口述资料撰写非洲史
以口述资料撰写非洲史并探索相关理论是范西纳对非洲史研究的最大贡献。1961年,范西纳出版了以法文撰写的《口述史学方法论》(De la tradition orale: essai de methode historique)。这本书很快引起国际性反响,随后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等出版。
在范西纳看来,口述资料是未被写出的信息,保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尽管它在当下被讲出,但它包含着来自过去的信息。口述资料和书面资料都是从过去传递到现在的信息,都能在重构过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口述资料能为其他资料提供印证,就像其他资料能为口述资料提供印证一样。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书面材料的情况下,口述资料必须在重构过去中发挥作用,尽管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口述资料的价值还在于,它可以提示我们应追索哪些问题,它能提出一些基本的假设,能指引进一步的研究。
范西纳对口述资料本身和将口述资料运用于非洲史研究进行了阐述。他对作为信息的口述资料的生成和传播进行了论述,强调将口述资料与其所在的社会相联系,结合起来互证分析。他对口述资料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将非洲的口述资料具体分为记忆性讲说、历史歌谣、个人传说、起源传说、史诗、故事、谚语、格言等多种形式,并通过分析其语言形式、内部结构和体裁风格来明确各自的意义和局限。他非常重视口述资料被接受的过程特别是在被接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强调口述资料的有效性和重要程度根据空间和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强调要考虑某些口述资料本身的时空信息缺失和神秘难懂,要考虑口头传说在传递过程中因记忆失败、控制性叙述和解释性篡改而造成的混乱或者失真。他强调口述资料必须实地搜集,要有一定长的时间在实地并掌握当地语言,要有效地认识所在的环境,而搜集和记录过程本身也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要注意通过比较来厘清针对同一对象而出现的不同说者和不同时空下的不一致,特别要注意避免说者和听者的理解不一致。
除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外,范西纳还对口述资料进行了具体运用,其主要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口述资料。
在《稀树草原诸王国》(Kingdoms of the Savanna)一书中,范西纳利用了从奔巴人(Bemba)、洛兹人(Lozi)、隆达人(Lunda)、卢巴人(Luba)、库巴人(Kuba)、伊姆班加拉人(Imbangala)和奥文本度人(Ovimbundu)等族群中获得的口述资料,包括统治者身边专司重大事件记录和讲述的官员以及坟墓守护者保存的口述资料、关于族群亲缘关系的口述资料、仪式描述资料、史诗性质的歌谣、起源神话、关于作物和某些贸易商品的传说等。通过这些口述资料,范西纳对稀树草原居民的物质文化、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宗教信仰等进行了勾画,对稀树草原上的古刚果王国(Congo Kingdom)、卢巴王国(Luba Kingdom)、库巴王国(Kuba Kingdom)、隆达王国(Lunda Kingdom)、恩东哥王国(Ndongo Kindom)、卡曾伯王国(Kazembe Kingdom)、洛兹王国(Lozi Kingdom)的兴起、演变和衰落进行了探讨,总结了稀树草原上主要王国的三个特征——统治者只在政治意义上具有最高地位、王位继承易引发内部冲突、王国的地方往往高度自治从而易于分离。此外,范西纳还结合来自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字资料对诸王国与外部力量(包括葡萄牙殖民者、荷兰殖民者、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的互动进行了分析。《稀树草原诸王国》一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大致包括今刚果(金)西部和中南部、今安哥拉北部和东北部以及今赞比亚西部、北部和东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历史,明确了刚果河流域古王国存在的切实性和其发展的内在独立性,对当时盛行的认为这一地区没有历史的论调作了强有力的驳斥。
在《现代卢旺达的前身:尼伊津亚王国》(Antecedents to Modern Rwanda:The Nyiginya Kingdom)一书中,范西纳利用了关于尼伊津亚王国的口述资料,包括官方掌控的宫廷仪式讲述资料、王朝诗歌、王系传承资料以及流传在民间的传说等。在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系统的起源传说。一个以传说中的“从天而降”的第一任国王基格瓦(Kigwa)为线索,另一个以缔造王国第一个繁荣时期的“文化英雄”基汉加(Kihanga)为中心,这两套传说包含尼伊津亚王国王系传承和社会发展及分层的信息。此外,还有关于多位国王的口述资料,特别是关于奠定王国基础的恩多里(Ndori)的口述资料。它讲述恩多里从北方来,携带大批牲畜,在今卢旺达中部地区获得大批支持者,他们一部分成为恩多里的“封臣”,一部分则以独立身份与恩多里结盟。在描述恩多里时期仪式的口述资料中,尼伊津亚王国的政治机制得到明确:恩多里的王庭为中央,通过给予牲畜使用权来吸纳和维系支持人群和武装队伍,各核心支持者定居点形成拱卫的地方,定期通过仪式向恩多里示忠。随后,范西纳又利用关于几位国王的口述资料,对尼伊津亚王国18世纪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扩张、19世纪的社会变动特别是19世纪末期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描述。以口述资料为基础,范西纳重现了尼伊津亚王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生活、政治进程和社会变动。
2010年出版的《被殖民者:刚果农村的库巴人,1880—1960》(Being Colonized:The Kuba Experience in Rural Congo,1880-1960)一书展现了范西纳对口述资料利用的一种新尝试。该书利用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库巴地区生活和观察的各种记录、殖民者的文字和图片材料、部分有文化的库巴人的文字记录等多种非口述资料,除此之外,才是各阶层各年龄段库巴人的口述资料。这实际上已不是以口述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但值得重视的是,该书试图从被殖民者的视角审视非洲的殖民主义历程,而在这方面,各阶层各年龄段库巴人的口述资料特别重要,是一种直接的以库巴人之口传述库巴人之史。“难道非洲人就没有他们自己的成就、梦想、欢乐和痛苦吗?难道他们就没有部分地被他们自身的殖民经历塑造吗?难道他们不是一群曾经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而且是现在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先辈吗?然而,殖民史没有强调非洲人的经历,没有把他们放在故事的中心——尽管他们明显属于这一故事。”此书的目的正在于从被殖民者的角度来叙述殖民,关注被殖民者的经历,强调他们的积极而非消极的地位,“让他们尽可能地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范西纳强调非洲口述资料的宝贵性,并坚持非洲史研究利用口述资料的必要性。但是,口述资料本身具有不可回避的主观性、不稳定性、易发生传递错误等缺陷,而且在非洲,口述资料还往往存在时空框架缺失的问题,特别是时间缺失。因此,学术界一直不乏对范西纳的质疑。最初,学术界对范西纳的工作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认为口述资料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因为那只是一种“当下表演的成果”(a product of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而不是“过去的遗产”(a heritage of the past),口述资料只是“传说”(fiction),不是“事实”(fact),而以口述资料为基础撰述的成果也就不可能是历史。随着范西纳研究工作的步步推进,学术界的态度有所转变,但仍持不同程度的保留。学术界愿意承认范西纳本人及其研究工作的出色卓异,但不完全认可其理论方法,更对其相关著作的可靠性存疑。在面对质疑时,范西纳初期的反应是极力辩争,但后来范西纳也不得不承认过分依赖口述资料的脆弱性,不得不正视非洲口述资料缺失时间框架这一“硬伤”。
尽管如此,范西纳仍然认为,口述资料的不足可以通过不懈地寻找其他资料来进行弥补。在范西纳看来,非洲史研究仍处在并且可能长期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口述资料是有不足,但一切还只是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非洲史研究要想真正达成以非洲的视角看非洲,恐怕还是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口述资料,因为相对于外部的文字资料而言,非洲的口述资料可能更能凸显非洲真实的过去和内在的价值。必须承认的是,非洲史研究有其特殊性,由于没有或几乎没有文字资料,重建非洲某些地区在某些时期的历史只能较多地依靠口述资料。

多学科、多资料结合探索非洲史研究
如上所述,对于范西纳以口述资料撰写非洲史,学术界始终有质疑,范西纳本人也意识到不足。实际上,范西纳本人在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乌特之子:库巴人的历史》(The Children of Woot: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一书以范西纳早年在库巴的亲身经历和搜集到的资料为基础。在这本书中,范西纳呈现出诸多口述资料运用的窘境:在讲到库巴人的起源史时,范西纳使用的口述资料有至少七个不同版本,却又找不到可以证明哪一个版本更加真实或者贴近真实的证据;在论及库巴人的迁徙扩张史时,范西纳大篇幅地陈述了从库巴人那里获得的口述资料,但最终却告知读者,这些口述资料所涉及的地理地形跟现实中的地理地形多有不符。随着研究的推进,范西纳明显地感觉到,如果只依靠口述资料,始终会有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为此,范西纳不断探索,尝试以多学科、多种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研究非洲史。
范西纳在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论述中就明确提出,考古学、文化史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都可以为非洲史研究提供很好的帮助。考古学可以通过对遗物的分析研究获得年代等方面的数据和关于族群原初历史、人口流动、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些信息可以与保存在口述资料中的信息进行印证。文化史学可以通过对古物、仪式、风俗、社会组织等进行比较研究,抓住其单位性特征,进而获取关于人口流动、族群间互动、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和政治社会机制等方面的信息。语言学可以通过对某些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寻找操相关语言的族群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特定地区的人口流动、族群间互动,特别是通过对某些表示作物、牲畜、商品、人物头衔、宗教性活动等的词汇进行分析,可以认识特定人群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体质人类学则通过对不同人群进行基因等方面的分析,比较确切地界定相关族群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流转。此外,一些自然科学的成果也可以运用,特别是一些可以有助于认识非洲某些地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的地理、地质、动植物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和一些有助于给出时间节点的天文学研究成果等。
根据自己的学科能力,结合自己长期在非洲生活和研究的实际,范西纳主要从文化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切入展开研究。
以文化史学方法研究非洲史,范西纳主要是从非洲社会留存的某些器物入手。《国王的铃铛》(The Bells of Kings)一文从分布于中南部非洲广大区域的多种铁制铃铛入手,分析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族群流动和互动。这篇文章发表于1969年,当时学者们已经在探讨和争论关于班图人迁徙和铁器文明在非洲传播的问题,并且已经意识到某些王国集群间存在联系,但苦于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口述资料比较零散且一些学者不乐于使用,民族志和语言学资料能提供一些证据但仍然不够充分,考古发现所得也非常少,因为本身非洲人使用的很多器物都难以长期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存在于相关区域的铁制铃铛可以说是最佳的研究切入对象。就铃铛本身而言,由于其为铁制,可以将其与铁器文明传播问题相关联;由于有些铃铛被用于政治意义上的通报和召集功能,可以将其与政治体制问题相关联。通过对比铃铛的形制和多种相关语言对铃铛的称谓进行总结、比对和分析,范西纳大致描绘了一条铃铛从几内亚湾西非地区经刚果河下游至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流转路线,这条路线与班图人从西非向中南非洲迁徙的部分路线重合,也与铁器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路线存在部分一致。由此,范西纳进一步对分布于相关区域的王国集群进行比较,初步地探讨了这些分布于几内亚湾西非、刚果河下游和赞比西河上游三块地区的王国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最终,范西纳确定这三者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从文化史学角度对语言学上早已提出的几内亚湾西非是班图人迁徙以及相关文明传播的起点的理论进行了证明。
以语言学方法研究非洲史,范西纳主要是基于三点:首先,语言学家对非洲语言进行的研究不断取得能启发并支撑非洲史研究的成果;其次,范西纳认为语言是过去的遗产,是一种“长期性的口述资料”;最后,由于长期在非洲生活和调查研究,范西纳本人比较擅长利用非洲语言资料。
19世纪,在非洲的欧洲殖民者发现,中南部非洲广大地区黑人居民的语言具有相似性。1886年,英国殖民者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明确提出,这些语言应是由某一共同语言演化而来。20世纪20年代,长期在非洲活动并对非洲语言进行研究的德国传教士戴德里希·威斯特尔曼(Diedrich Westermann)提出,班图诸语言和西非地区语言之间多有联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通过大量的搜集和比较,对非洲语言进行了分类。格林伯格确证了威斯特尔曼所言的班图人诸语言和西非地区语言之间的联系,并将相关区域的语言归入他命名的“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在这些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语言来重构中南部非洲的历史成为非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范西纳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在《雨林中的路:赤道非洲政治传统史》(Paths in the Rainforests: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一书中,范西纳对赤道非洲的历史进行了重现。在此书出现之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赤道非洲地区环境恶劣,这里的居民只是不断地努力维持生存,他们有的只是人口数量的变动和人群的流动,没有历史。而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承认这一地区有历史,那么在通常性的资料如此缺乏的情况下,又该如何重现?如果无法重现的话,那么这一地区还是只能说没有历史。对此,范西纳指出,语言是附着于事物的标签,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语言来认识事物的形式与内容,通过认识语言的变与不变来认识事物的变与不变。这样的话,通过对赤道非洲地区居民的语言进行研究,就可能获知这一地区的历史。范西纳对赤道非洲地区的147种语言中的词进行比较研究,他将这些词按所指分成九类:社会单位(social units)、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社会活动(social activities)、食物生产的技术与工具(food production:techniques and tools)、驯化植物与动物(domestic plants and animals)、制造业的技术与工具(industries:techniques and tools)、交换(exchange)、灵与力(spirits and forces)、宗教人员与活动(religious experts and activities),以此重现赤道非洲地区黑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以及宗教观念和形式,并演绎这一地区的政治传统发展。此书告诉人们,广阔的赤道雨林地区绝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抹绿色,它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单一的,它可以划分成约200个次区域社会,它们各不相同,每一个次区域社会自身也很复杂,这里除了人口数量的变动和人群的流动外,还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动,也有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迁。
在《社会如何产生:1600年前中西部非洲的政制》(How Societies are Born:Governance in West Central Africa before 1600)一书中,范西纳通过对中西部非洲黑人居民的语言进行搜集和比较研究,重构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史并探讨了这一地区政治体的发生发展史。这一地区黑人所操语言属班图语的一支,称“恩吉拉语”(Njila),操原恩吉拉语(ProtoNjila)的人群居住在今刚果(金)的基韦鲁河流域中部(Middle Kwilu)。在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00年前后的约800年时间里,恩吉拉语从基韦鲁河流域中部地区传播到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东部地区,亦即从今刚果(金)中西部到今纳米比亚北部—博茨瓦纳西北部一带。这样,在语言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中西部非洲的轮廓就被勾画出来。而在公元700年到公元1000年间,在中西部非洲出现了辐射范围包括今安哥拉、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接界地带的贸易中心迪乌尤(Divuyu),产生了以高粱和小米为主要种植作物的农业、以牛为主要牲畜的牧业。随后,直到公元1600年这段时间里,这里的社会政治组织从村庄发展成酋邦,开始出现集中化的权力层级和体系以及表达此种权力和体系的称号、象征物品、观念等。
对这一段历史的重构,范西纳主要依靠的就是恩吉拉语中的词汇。通过指代林中和草地中田地、多种块茎作物、酒棕、鱼、鱼线、鱼钩、独木舟、陶工以及表达“种植”、“划桨”、“获取食盐”、“加工石或木”、“编”、“织”意义的词,范西纳指出,操恩吉拉语者曾居住在靠近河谷的雨林地区,他们既种植作物,也从事渔业,同时还有多种手工业;指代户、火塘和议事屋等的词以及表示群体、亲属等的词,则可以表明存在由一定数量人口组成的家庭以及更进一步的村社共同体;而根据酋长指代词汇的传播和语音变迁以及逐渐出现“次级酋长”“地区酋长”“贡品”等意义词汇以及包含“首都”含义词汇的情况,范西纳也构拟出这一地区的政治发展历程;此外,还有表示社会和宗教生活的指代仪式、灵媒、治愈者、符咒、神祠以及表示“被施巫术”意义的词等,通过这些词又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这里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又恰恰与政制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如何产生:1600年前中西部非洲的政制》这本书虽然是以语言资料为基础,但它所研究的地区恰好有几处得到较好发掘和研究的遗址,包括位于今博茨瓦纳西北边境靠近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迪乌尤遗址、恩科马遗址(Nqoma)以及位于今安哥拉境内库尼尼河(Cunene River)畔的菲提(Feti)遗址。在这几个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范西纳以语言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辅证和互证,可以说也是范西纳多学科、多资料结合研究非洲史的一种有效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在范西纳看来,多资料不仅意味着多种学科来源的资料,还意味着以多种形式存在或呈现的资料。在《被殖民:刚果农村的库巴人,1880—1960年》一书中,范西纳除了利用多种类型的库巴人的口述资料外,还利用了自身在库巴地区生活和观察的各种记录、部分有一定读写能力的库巴人的文字资料、殖民官员、传教士、商人的文字和图片材料等。
范西纳的贡献与局限
范西纳是现代非洲史研究第一代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与罗兰·奥利弗、约翰·费奇、菲利普·柯廷等欧美学者以及肯尼斯·戴克、巴斯维尔·奥戈特等非洲学者一道,奠定了现代非洲史研究的基础,开创了现代非洲史研究的局面。
在这段开拓性的历程中,范西纳贡献了以口述资料、非洲器物、非洲语言资料研究非洲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成果,使非洲史研究得以突出外界不屑和怀疑的重围。直到现在,非洲史研究工作者仍然把口述资料当作非洲史研究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和一种不容忽视的研究路径;而语言资料之于非洲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则已得到广泛承认,由于相对于口述资料而言具有更充分的客观有效性,利用语言资料已经成为有效提升非洲史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范西纳贡献了包括刚果河流域地区、大湖地区、赤道地区在内的非洲广大地区的历史研究成果,使这些一度被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史家认为“无历史”的地区变成有历史,既推翻了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设置的学术壁垒,也开辟了对这些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的道路。更具说服力的是,范西纳所贡献的关于这些地区的研究成果所承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促使人们去正视和重视。
但是,范西纳的非洲史研究也有其局限。首先,口述资料有其固有的缺陷,单凭或者主要凭口述资料无法有效支撑一部历史。范西纳早期坚持口述资料的充分有效性,后来则坚持非洲史不得不倚重口述资料的合理性。尽管我们承认非洲史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在非洲史研究浸染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纠葛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容许非洲史研究者比较多地利用口述资料,但这种容许不应是全面的,更不应是永久性的。
其次,语言资料固然比口述资料更具客观有效性,但却存在有效时间框架缺失的问题。以语言变迁来考察非洲历史,特别是殖民时代前的历史,往往需要以百年乃至千年为单位。我们通过语言可以知道经过数百年或数千年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却无法明了这数百年或数千年间的具体情况,这样的历史未免太过粗略。即便可有所谓宏观历史,但真正有效的宏观历史从来都应是建立在中观和微观历史基础之上。非洲史和非洲历史语言学学者克里斯托弗·埃赫雷特(Christopher Ehret)盛赞《雨林中的路:赤道非洲政治传统史》这本书,称其写出了赤道雨林地区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000年的历史。但这所谓的“4000年”历史,中间只有粗略而不可靠的阶段划分,基本没有具体的时间,也缺失具体的人物和历史事件。
再次,作为一位与非洲有深刻关联的学者,范西纳对非洲充满感情。在非洲史研究中,范西纳所持的往往是一种“为非洲辩护”的态度,这表现为一方面,他不容他人贬低非洲和非洲史,另一方面,在有效证据有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他仍竭力撰写相关历史。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刻意贬低非洲史类似,“为非洲辩护”实际上也不可取。就非洲史研究而言,应该承认某些资料严重缺失以及由于这种缺失而导致的无法写史或无法充分写史的客观现实。
必须强调的是,范西纳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局限很大程度上有客观原因。就此而言,他尽力克服这些客观困难而做出的贡献就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仍然要实事求是,看清楚局限,方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
本文作者刘伟才,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