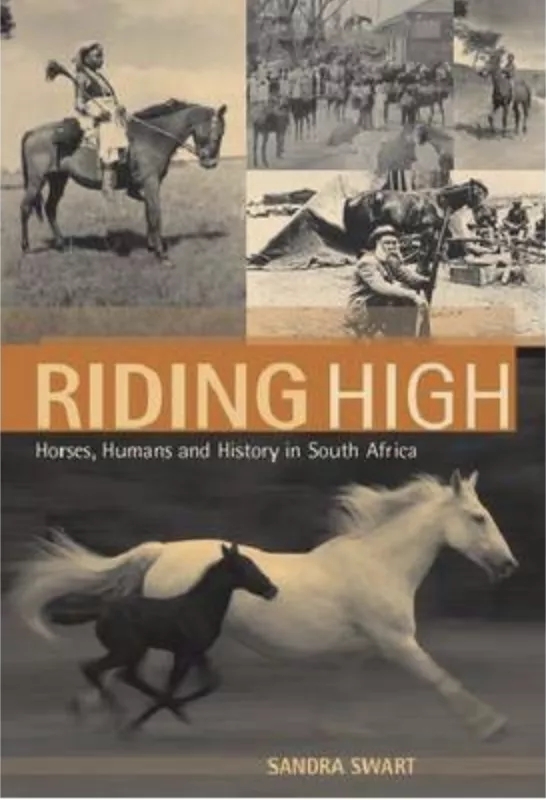桑德拉·斯沃特(Sandra Swart)是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教授、世界环境史组织联盟常务理事、南部非洲历史学会前任主席,她毕业于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环境史教授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inart)。作为杰出的女性环境史学家,桑德拉致力于非洲环境史研究,尤其是动物与环境史的相关研究,在南部非洲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她的代表作包括Riding High: Horses, Humans and History in South Africa(《骑上马:马、人、南非史》)[1]、Writing Animals into African History(《把动物写进非洲史》)[2]等。2021年5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费晟教授邀请桑德拉进行了一次线上讲座,笔者在此次讲座前后和她就其学术经历、对非洲环境史研究的参与和观察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交流,此文即基于这些对话的主要内容整理。
桑德拉·斯沃特教授和她的马阿兹特克(Aztec)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您是如何关注到环境史及其与动物的关系的?这是否和您的学术经历有关? 桑德拉 · 斯沃特:我喜欢这样描述自己:“桑德拉 · 斯沃特是一只自由放养的灵长类动物,也是斯泰伦博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她于 2001 年在牛津大学获得现代历史博士学位,同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环境变化与管理硕士学位。她对南部非洲的社会和环境历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文章,特别关注人类与动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大家其实很容易在网络上找到我的学术简历,但我的生活有很多维度: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我的很多学术时光留在了演讲厅里;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在世界各地落满尘埃的档案馆中查阅资料;但最令我兴奋的是我的田野调查通常是骑马驰骋在南非、莱索托、美国西部和蒙古国的土地上。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它讲述了20 世纪末一位孤独的南非阿非利加语诗人在野外研究一群狒狒的故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野外灵长类动物学研究案例,但是在结束对这一案例的研究后,我发现自己对狒狒比对诗人更感兴趣,我甚至在狒狒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更多诗意的存在。因此,我在完成博士学业的同时,又攻读了环境变化与管理的硕士学位。牛津大学非常慷慨,不仅免除了我的学费,还让我从专业上对动物生态学有了一些了解。 当我在斯坦林布什大学获得第一份工作时,我意识到,我将一生致力于了解人类和动物长期纠缠的历史。 我首先写了马,以及它们进入非洲南部后如何改变的一切。起初的研究让我觉得自己很孤单,尽管我联合我的研究生们一起很快建立了一个有关狗、企鹅、猫、牛、蜱、野生动物和流行病研究的“动物园”。但毕竟之前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研究,尤其是当时全世界研究非洲历史的人都很少,更别提其中关于动物历史的研究了。但是当然,我没有被吓退。要知道,很多新兴学科在刚起步时都是如此,但后来的前景仍然光明:工人阶级史、妇女史、非洲史,都是这样。 我知道您对自然保育做过很多调研,可以谈谈对此的心得吗? 桑德拉 · 斯沃特:自然保育的术语使用现在已经比较规范了,不像19世纪后期,那时“保护野生动物”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自然保育是一个与保护区、野生动物(无关猫、狗或猪的福祉)都相关的问题。它不只与野生动物有关,也不仅仅停留在动物保护上,还意味着要保护它们生存的栖息地、领地。这才是我所谓的自然保育,这也是其在非洲语境下的真正含义。 当然,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认知并不是必然的或术语层面的。自然保育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决定了我们应采取什么方法和态度来保护动物,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牲畜。 我去几个自然保育区做过调研,在南非,一个典型代表是克鲁格国家公园,另外还有不少野生动物禁猎区(Game Reserve)。我去过的几个中,一个位于南非西部,与莫桑比克边境接壤,规模堪比一个小国家;另一个是卡拉哈里(Kgalagadi)保护区,它跨越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我们称它为“跨界公园”。作为历史学家,当我去这些地方做调研的时候,始终要搞清楚几个核心的问题:自然保育区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规模堪比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禁猎区?如何管理跨越三个不同国家的野生动物禁猎区?——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是必然的,是某些历史时刻造就了它们。 进入禁猎区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也要服从专门的管理,防止因随意上下游览车招致人身伤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克鲁格公园,每年都有人因为从莫桑比克非法入境被野生动物攻击而遇害。这时,关于自然保护区应遵从自然边界还是国家边界的讨论就会出现,也让类似的关于国家公园的讨论极具政治色彩。
Riding High Sandra Scott Swart / 著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0 根据您的研究,关于自然保育的历史研究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桑德拉 · 斯沃特:我把对自然保育的历史研究分为传统叙事方式和新的跨学科研究方式两种。 第一种方式也即那种所谓的“退化叙事”(a whitewashed version)。传统叙事中的很多种族歧视故事采取的是白人的叙事(a white story)方式,通常讲述白人如何用武装保护野生动物、对抗(对象主要是)黑人偷猎者。其中流传甚广的传言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斑驴几近消失殆尽,白人们说,这类野生动物的灭绝都归咎于非洲的黑人猎杀。在19世纪末斑驴(quagga)几近消失殆尽时,白人将这类野生动物的灭绝主要归咎到非洲黑人身上。 但作为历史学家,我通过研究发现,让这种野生动物灭绝的并不是本土的非洲人,而是白人捕猎者——阿非利卡人、布尔人以及来自欧洲的狩猎者,是他们在猎杀和食用这些野生动物的肉类,享用由它们的皮毛制成的奢侈品,鞋子、皮包、帽子和其他东西。其中,许多捕猎者是来自海外的竞奖猎人(trophies hunters),他们到非洲展开猎杀的竞技活动只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进行炫耀。 白人、武装的白人变成“真正的英雄”,使得关于自然保育的第一种传统研究成为“成功者的叙事”。当然,导致野生动物灭绝的还有其他原因,如畜牧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一方面有助于牧场主和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招致野生动物不断消亡。如果回溯更长时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黑人狩猎者在非洲生活了数千年(至少5000年),野生动物也一直在那里生活。导致野生动物灭绝的罪魁祸首不是他们! 实际上,对物种灭绝的思考是历史性的,大概直到19世纪,人们才意识到之前破坏土地导致庞大的动植物群落灭绝事态演变的严重性。其中,关于“益畜”和“害畜”的判断标准也发生了改变,这当然是因为人们对更大的生态系统有了更多认知。一个成功的保育案例来自20世纪初,当时白犀牛在南非东南部只剩下20头,一些“白人英雄”开始着手对其进行保护。现在南非有两万头白犀牛,你不得不承认,当这些白犀牛作为最主要的生物群落被保护时,所谓的堡垒保育(fortress conservation)奏效了,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成功故事! 当然,“堡垒”也有其政治争议,这意味着动物被圈在围栏里,只允许一些付费的游客、武装的野生动物禁猎区守卫进入,偷盗者或者贫困的非洲狩猎者将被逮捕或射杀。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南非,直到20世纪70年代,南非人民才被允许进入和享受国家公园。这也导向了第二种叙事方式,即反思如果我们不把非洲人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不只把他们当作偷盗者,还想从历史中学到更多东西,这样的话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叙述?也许我们这时就可以看到,在非洲历史中,图腾动物(totem animal)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动物。我将这种行为称为“无意保护”,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有意识的保护动物,但它是个令人开心的巧合。 最后是我正在使用的研究方式,我把它视为第三种自然保育的叙事方式,即跨学科的自然叙事。我认为在这样的叙事方法中,不能只讲野生动物禁猎区,也要探讨城市和郊区的动物再野化。作为历史学家,我非常认真地看待动物,想把动物放在一个叙事的核心位置。我不想再探讨诸如大象、狮子和长颈鹿之类的漂亮动物,我想探讨那些不漂亮的、在之前的自然保育中未被提到的、非比寻常的动物(比如狒狒)的历史。正如我在中山大学的费晟教授组织的讲座中提到的那些故事一样,我认为从这些被忽视的历史中,不仅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的抗争故事,看到再造、强化父权制主导的现实,还可以看到人类心理生态学的阴暗面(the dark ecology of humans psychic),等等。 我们都知道,差异不只存在于物种之间,也存在于同一物种的不同代际之间,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自然保育 。
桑德拉·斯沃特教授在蒙古国做田野调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据您观察,非洲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有哪些?非洲对世界环境史产生了哪些影响?您致力于推进怎样的环境史研究? 桑德拉 · 斯沃特:这些问题都很引人入胜!上一代非洲环境历史学家比较关注三个“C”——殖民主义(Colonialism)、保护主义(Conservatism)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他们批评白人殖民者和殖民主义对非洲农业景观的影响,这些殖民者如何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破坏了原住民对土地的管理,并迫使非洲人进入荒野——那些积压的、过度放牧的土地。这些历史学家展示了堡垒保护的形成,以及这样的壁垒又如何迫使非洲人离开自己的土地去创造新的荒野——这种范式认为,需要强行驱逐当地人,才可以为野生动物腾出空间。这样的野生动物发展或者保护区的建立,是以高栅栏和武装警卫保护为典型特征的,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种基于殖民主义的保护模式,并在殖民主义结束后持续了很长时间。 当代的非洲环境历史学家,则在揭露人类未触及的、“纯的”或“野生的”自然是如何变为“没有人的自然”的危险神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没有人的自然”的神话,后来成为特别保护界限和壁垒设置的基石,也引发了大众对“自然”的非历史性思考。 实际上,生态系统是动态变化的。正如南非历史所揭示的那样,原住民被暴力强迫迁离也是环境史的一部分。自 1968 年以来,由加勒特 · 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模型在南非的历史中得到了证明。“公地悲剧”表明,每当人类获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机会时,就会为此而相互争斗,直到自然资源被摧毁或耗尽。这个理论表明,为了拯救自然,我们要么需要完全的国家控制,要么需要彻底的资本主义私有化。 环保主义者和政治家相信哈丁的模型,并采取了完全的国家控制或完全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强硬方法。幸运的是,埃莉诺 ·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其后辈将“公地悲剧”的历史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他们用过去的经验证明,许多人群在历史上使用了大量不同的地方策略,从而避免了“公地悲剧”。 从历史上看,一些非洲社会设计和建设了自己的公地边界,对成本和平衡做出了基于本土经验的判断,并思考了自己的绩效和解决冲突的方法。我们看到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模式的兴起,例如津巴布韦的 “公共区域本土资源管理”(CAMPFIRE)计划[3]等。这说明本土的机制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当今环境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在于探索“自然”的本土管理—这强调了准确的环境史可以对社会产生价值,这也是我的灵感来源。 当然,非洲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包括更广泛的焦点,如鼓励重新关注前殖民时代、通过包括“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的镜头来审视过去,以及通过恢复原住民知识或当地环境知识和管理方法来重塑环境史,等等。 令人高兴的是,非洲环境史学界目前也开始认真地对待“动物历史”了。尤其是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下,人畜共患病已经扰乱了地球。 在您看来,中国和南非的环境史研究如何相互借鉴? 桑德拉 · 斯沃特:我期待与中国学者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我认为,应该做更多的比较研究、跨洲际研究和学术交流。 首先,目前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很紧密,在诸多环境问题上都有关联——在贸易和自然矿产的开发中产生的很多问题,需要学者进行认真的环境史研究。 其次,“人类世”确实需要非洲和亚洲的学者将其作为一个时代、一个话语、一个政治时刻和一个历史进程来审问、明辨。目前,关于人类世的大部分对话都来自并集中于北半球,为了使其成为一个更全球化的对话,非常有必要加强中非环境史研究的互鉴。 我刚刚与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蔡元丰副教授一起,被任命为博睿(Brill)出版社全新系列丛书的共同编辑,我们即将进行“非洲和亚洲人类世:环境人文研究”丛书的编纂,也很期待其他中国学者能参与其中。 注 释 [1] SWART S. Riding High: Horses, Humans and History in South Africa[M].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SWART S. Writing Animals into African History[J]. Critical African Studies, 2016, 8(2): 95-108. [3] “公共区域本土资源管理”(CAMPFIRE)是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计划,它是津巴布韦首批将野生动物视为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计划之一,同时解决了将其所有权分配给保护区内和周围的原住民的问题。1975年,津巴布韦《公园和野生动物法》为CAMPFIRE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该法案允许社区和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其土地上使用野生动物,这意味着之前无视区域、放任利用野生动物的殖民政策被改变了。1989年,这一计划由津巴布韦政府发起,并由津巴布韦国家农村地区议会(RDC)管理。虽然还是有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没有完全得到保护,但该计划旨在通过管理狩猎、减少非法偷猎、环境保护和创收来加强社区的经济前景,从长远来看支持了各动物种群的持续发展。目前,该计划已在津巴布韦得到广泛实施,涵盖了津巴布韦 57 个地区中的 36 个。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