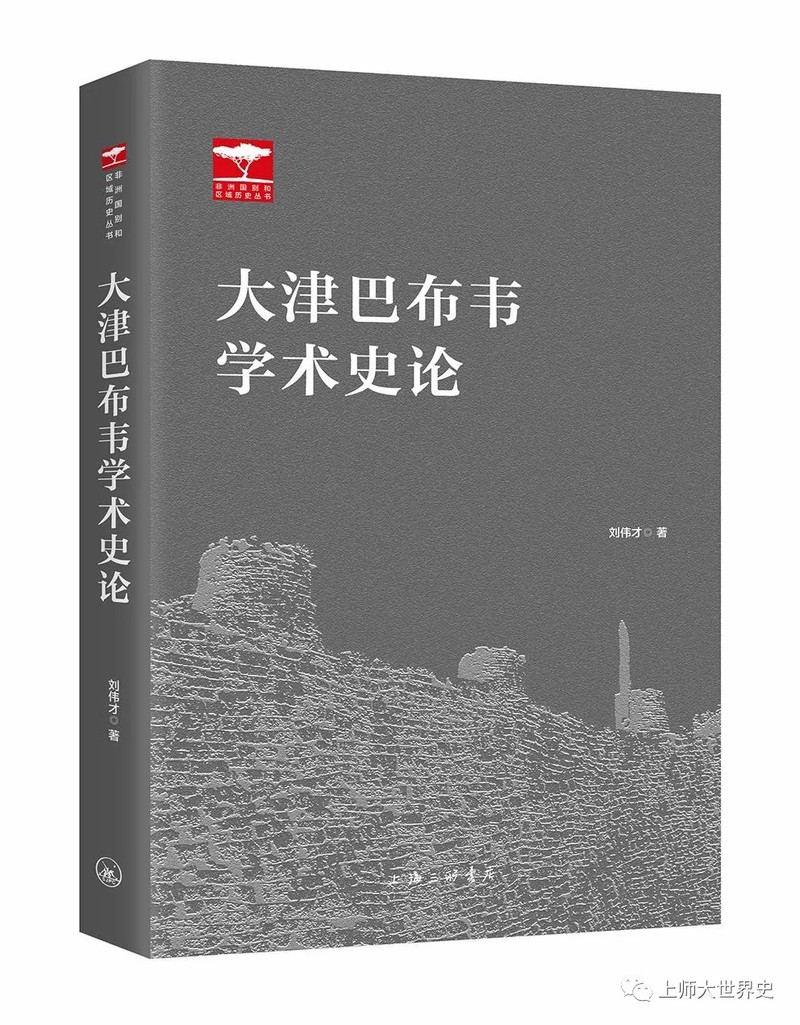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非洲国别和区域历史丛书”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5月版
大津巴布韦是非洲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非洲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影响下,欧美世界曾长期否认黑人是大津巴布韦的建造者,并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含米特论”。考古研究后来证明了黑人是建造者,但由于资料缺乏和遗址本身的原因,诸多细节仍不明晰,质疑和争议始终存在。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津巴布韦问题又开始陷入黑人民族主义的漩涡。黑人认定黑人是建造者,他们以此为基础对相关历史进行多种形式的演绎乃至编造,他们刻意地拔高大津巴布韦的建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他们反对任何对黑人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质疑,将种种质疑不由分说地与种族主义挂钩。从学术上来说,大津巴布韦问题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白人种族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的交织影响却使大津巴布韦问题超越了学术的范畴,“政治正确”的逻辑更是使大津巴布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禁区。《大津巴布韦学术史论》一书试图从学术史的层面寻求对诸多问题进行厘清: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仍未解决?哪些问题并未解决但却在黑人民族主义和“政治正确”的影响下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大津巴布韦学术史论》将围绕大津巴布韦的探索和研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71年至1905年。具体为从毛赫(Karl Mauch)的“发现”至兰道尔—麦基弗的研究发布之前。在这一阶段,以本特(Theodore Bent)和霍尔(Richard Hall)为代表的人士开辟了“含米特论”的基本路径,尽管他们的研究后来被证明错误较多,但二人的影响力却从未消失,无论是反对还是承认,都无法绕开这二人。第二阶段为1905年至1961年。具体为兰道尔—麦基弗(David Randall-MacIver)的研究发布至萨默斯(Roger Summers)、罗宾逊(Keith Radcliffe Robinson)和维提(Anthony Whitty)1958年发掘和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中间还有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的决定性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三次专业性的考古,从科学的层面对基本问题进行了厘清和论述,尽管在细节上仍有很多不足和一些悬而未决且不断面临“含米特论”者的攻击,但关于“建造者为黑人”(Bantu origin)和“建造时间为中世纪”(Medieval date)的基本论断已立住阵脚。第三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以萨默斯和加雷克(Peter Garlake)为代表的学者,在立足既有考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结合部分文献、口述资料和人类学资料等,对围绕大津巴布韦的探索历程进行了梳理,对大津巴布韦本身及相关石建遗址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并对围绕大津巴布韦的历史进行了谨慎的构建。第四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见证了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向黑人多数统治的津巴布韦共和国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之下,黑人立意要构建有利于加强黑人民族认同和自尊的“官方史学”。在这一阶段,逐渐出现了一系列强调黑人主体性的成果,比奇(David Beach)从绍纳人传统入手,穆登奇(Stan I. G. Mudenge)选择莫诺莫塔帕国家为切入点,胡夫曼(Thomas Huffman)则注重从非洲传统文化发微,部分研究虽然是演绎但仍可称谨慎,但也有部分研究出现了编造过度的倾向。第五阶段为进入21世纪以来。进入21世纪后,新的一代学者崛起,新的技术和设备也使新的研究成为可能,尽管津巴布韦共和国的发展形势不佳乃至恶化,但对以往的发现进行再分析和对遗址进行再发掘仍被提上日程并慢慢展开。在这一阶段,以皮吉拉伊(Innocent Pikirayi)和奇里库雷(Shadreck Chirikure)为代表的学者利用多种新手段进行研究,为大津巴布韦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新空间。通过对五个阶段探索和研究的系统回顾,《大津巴布韦学术史论》提出,关于大津巴布韦,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仍没有真正地得到解决。基本上,“什么时候建的”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谁建的”这个问题从轮廓上解决了——是黑人,但是具体是哪一群黑人却无法毫无疑义地确定。而“怎么建的”“建来作何用”“因何原因被废弃”“为什么后来不建了”“为什么后来不会建了”等仍是定论少,猜测多,争议难断。特别是“怎么建的”这个具体问题,它涉及的主要是物质的技术,只要在技术上说不通或者无法证明,就都只能存疑。也正是因为如此,“含米特论”一直有市场,《大津巴布韦学术史论》也对诸种含米特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必须指出的是,有些“含米特论”显得荒诞,但有些“含米特论”却也可称有理有据。
非洲历史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且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而大津巴布韦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就是这种初级阶段的一种缩影:大津巴布韦问题经约一个半世纪而仍未有效解决,这是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大津巴布韦问题虽仍未有效解决,但一些力量却强制性地给出一些定论,并以某些主义相要挟,这也是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大津巴布韦上移开,把视野扩展到更广泛的全非洲,则会发现,在非洲史研究的范畴内,如大津巴布韦这样包含很多未决问题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于非洲史前文明的情况,我们仍只能给出一些参考性的框架和少数几个点的具体研究;对于非洲古代史的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如铁器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班图语人群的扩散、中南部非洲广大内陆早期主要政治经济实体的产生发展等或仍有争议,或仍需要填充空白或者空隙;即便是到了近代,一些地区性或国家性的重大历史进程或重大历史事件的部分细节仍付诸阙如。然而,某些主义和“政治正确”逻辑的制约是客观存在的。为了突破或者避开这些制约,非洲史研究特别是非洲古代史研究正在不断地探索多学科的道路,特别是注重用非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以期以自然科学性质的结论和数据荡开“主义”的干扰——这是当下和未来非洲历史研究前进的一个基本方向。